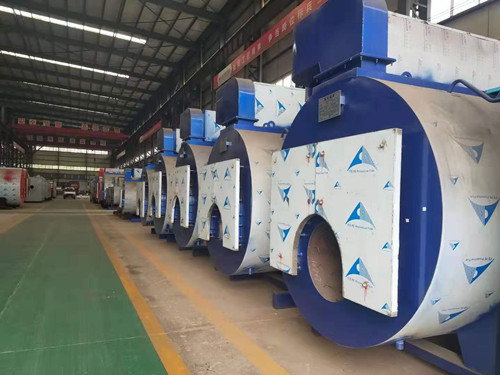七小时
外婆病了,我从急诊到家了。心衰,糖尿病外加年老免疫力衰弱各种机能下降,却没有打救护车,是舅舅开车从村里带到市里医院就诊。我妈接到
外婆病了,我从急诊到家了。
心衰,糖尿病外加年老免疫力衰弱各种机能下降,却没有打救护车,是舅舅开车从村里带到市里医院就诊。我妈接到电话,表现冷静,我以为没有那么严重,但第一时间收拾东西上医院准备和他们汇合。去时门诊在休息,看着舅舅搀扶已经气喘头晕仿佛下一秒就要休克的姥姥往门诊来时,我和爸妈急了,决定租轮椅立马送去急诊。两分钟路程说实话都要了我外婆半条命。
下午一点半,挂号,安排床位,上心电监护仪,缴费,输液,血检,尿检,ct,我只参与了跑腿的份。急诊室内规定只留两人看护,我妈和我舅舅守在床边,我和我爸则在外帮忙拿化验单。
前四个小时急诊来来往往,有人腹痛倒地,有人意外被割伤,有胃出血昏迷,有孩子被烫伤,有情侣因不合闹意见动手女方被重伤,有头部受伤…本就没留意这些人,外婆的情况已把我急得焦头烂额,所以其他人我并没有太多心思,甚至看了也自我安慰道:健康人谁来急诊呢?稍微休息时我妈递出话说外婆情况已经平稳还需要观察再说,我心中也放松了一点,等的实在无聊居然还打了把游戏。
傍晚五点,我姐和大姨带饭来,大致了解了一下外婆病情,大姨替换舅舅休息,我妈也顺利将检尿样给我让送去检验科,我姐陪我上二楼化验室。
晚上七点,急诊外开始骚动,安检大门全部外敞,几个护士在大厅等候,粗略打听了一下,120有重症患者将送来,我爸见混乱支开我和我姐去别的地方等不要挤在急诊外。我俩准备去熄灯的门诊大楼“避难”,昏暗中还和妹妹视频简单说了外婆病情。
晚上七点二十,回到急诊大厅,啜泣哀嚎声充斥大厅,乍一听以为是个女人的声音,但他蹲在急诊室门口,双手抱脸,确定是个男人。然后就是进进出出的医生护士,气氛有些低沉。大厅角落我爸悄悄说被送来病患的情况,据说是三十五岁产妇有妊娠高血压等疾病,心脏问题,来时昏迷,极力抢救中。男人是她老公,大女儿现坐在急诊大厅椅子上默默哭泣,她手指飞快敲打键盘,我猜是在告知其他家属或与朋友倾诉。我找了一个离她很近的座位坐下,我包里有纸巾,可那一瞬间不知道以什么方式给她。
晚上七点三十分,我妈出急诊室告知外婆住院已办好,但医生们都忙于抢救孕妇,顾不上外婆转离急诊,然后我妈又匆匆回了急诊室照看。
晚上七点三十五,我猜的,因为手机没有电关机了。女孩的哭泣没有停止隐隐约约吸着鼻子,我不敢看她。可心电监护仪的声音很清楚,具体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器,是能听到心跳轨迹的滴滴声,急促的滴滴声想起那么几下,然后长鸣持续了很久,我认为很久,那长鸣声引起我的耳鸣,莫名的闷气感和局促不安油然而生。时隔不到两分钟,医生告知孕妇老公和其大女儿,抢救无效,女人和腹中胎儿去世,一尸两命。逝者母亲也赶到,得知情况坐在急诊大厅放声大哭,我和姐姐无言相视,见不得这种场景,默默选择去旁边角落。
仅仅五分钟两条生命线画在一个终点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非亲属的死亡,明明与自己无关却也感觉到很大的无力感,甚至有点恨这无力。人只有在无能为力时才会检讨自己,发出看似无病呻吟多管闲事实则在嘲讽自己的感叹。这个大厅现在的气氛仿佛在慢慢吞噬自己的理智情绪,既悲伤又遗憾还夹杂着冲动,是那种想反抗的冲动,也可以说是不服的冲动。即便参与救治中的每个人都努力了,怎么最后还是去到了最坏的结果。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共情感,好像不只是我而是在这大厅所有沉默的看客。
八点十分左右,还是我猜的时间。外婆被急诊医生带路转移到住院处。因疫情只能少数人前往病房收拾东西,我和姐姐被留在住院底楼等候,刚经历过同是女性并目睹非亲属死亡而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我俩才有了交谈体会的时间。我知道不能评价别人的生命,可身心不适感太过明显,又在这样的压抑的气氛下,不得不开口聊几句。显然对于我这个未婚的姐姐刚看到的种种无疑只能加剧她恐婚和恐育的心理,而我憋了半天却说出“”每个人的命”这样的蠢话…说蠢不是因为我无以言表,而是我选择用这种“”大概率”的好听话来自欺欺人,人命天注定这种话能安慰现在像我这样的“”蠢人”。
七小时的陪护等来外婆住院继续观察,病情也慢慢稳定的欣慰结果。欣慰么?欣慰。可是明明是充斥着无名的尴尬和惭愧…
晚上九点半到家,我到了,她和孩子没到,至此之后的每一天永远到不了。急诊大厅里的人急诊室内的人,医生护士,腹痛倒地的人,意外割伤的人,酗酒胃出血昏迷的人,被烫伤的孩子,重伤的女人,家暴的男人,头部受伤的人,爸妈,舅舅,姐姐和大姨,我的外婆……我们都还活着,心电监护仪能检测到我们有力的心跳,目前不会急促滴滴作响也不会长鸣。痛哭的老人,像女人一样啜泣哀嚎的男人,无声流泪的大女儿,他们几点回家?七小时后…还是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