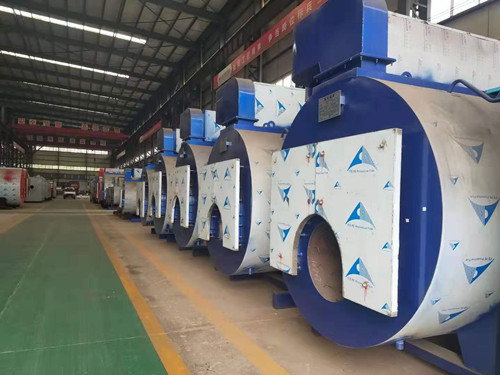石墩
“那个在门口垃圾堆旁边圆石墩上坐着的老太太呢?”“听说她已经死了”说实话那个老太太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奶奶让我喊她“大大
“那个在门口垃圾堆旁边圆石墩上坐着的老太太呢?”
“听说她已经死了”
说实话那个老太太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奶奶让我喊她“大大”,具体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她大概也有八九十岁了,差不多是个聋子,也是个瞎子。
小时候每次回奶奶家路过的时候总是看见她靠坐在家门口的圆形的石墩上,双手支着一根只有把手处油光锃亮的拐杖,黑黄的皮肤,满脸的皱纹,眼睛好像闭着又感觉像是睁着。
村里的巷子很窄,也不知道她是在张望什么,或是在听什么。有人骑车从巷子里穿过,有几个孩子嬉闹的在巷子里跑来跑去,或是当有野狗野猫跑去垃圾堆找食物时,老人总是会抬起头张望一下,眼睛已经在岁月的风蚀下有些睁不开,但她还是要使劲梗起脖子,试图把更多的东西收进自己的眼里。她看一眼,又把脖子收回来,眼睛接着似闭非闭,刚才那一眼似乎太累了,要赶快合上休息休息。
那时候我还小,路过那里的时候我会大声的叫一声:大大——,然后老人会抬起来头,高兴的说一声:哎—。那拖着长音的、沙哑的、现在想起来有些亲切的一声哎,在当时是多么的平淡和自然。这样简短的对话,好像不曾在那样平淡的像白水一样的日子里发生过。还有一次我路过时叫了一声大大,可能是声音比较小,她没有抬头,我又大声叫了一次,她抬起头,又是一次拖长的“哎”。奶奶恰巧在我旁边,跟我说,她年纪太大了,早就已经听不见了。原来她之前感觉周围的声音,可能都是一种混沌的、模糊不清的空气的振动。她的眼睛也是混浊的,可能那时候她眼里的世界,都只是一些个模糊的影子,但是至少她应该能觉到光亮,感知黑夜和白天,早晨或傍晚。
老人早起很早就出来坐着了,中午她家里人把她叫回去吃饭,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家人。有一天奶奶蒸了黄色的玉米面的团子,我记不清了,总之又大又圆还特别软,问起来有一股香味。奶奶拿了两个让我去给外面的那个“大大”,我拿着就窜出去,递给她。老人还是费劲的梗起脖子抬起头看,那双混浊的眼睛看不出什么光亮,现在我觉得她可能是患了白内障。她看了一会儿就接住那两个团子,她笑了,嘴里只有几颗牙了,嘴里还含糊不清的嘟囔着什么、其中好像是夹杂着一句家乡话的谢谢。那时候送完了就急忙跑回家吃饭了,现在想想,她没有什么牙,该怎么吃啊?是泡着米粥吃,还是如何吃。反正肯定没有牙齿完整的吃着香。
中间有许多年,回奶奶家路过那个巷子。老人有时候坐在石墩上,有时候不在,有时候又只剩下油乎乎还带着黑泥的拐杖在。仿佛她似有似无,她在的时候瞥见了看一眼,她不在时也不会让人想起那个石墩都位置应该有什么人。对于别人,甚至对于她的家人,都可能是无关紧要、若有若无的。在眼前时会想起来,可能还有这么个人。她不在眼前时,你根本想不起来她。那个看不清、听不清的老人,有些动静还非要梗起脖子瞧一瞧的老人,就像白天的圆石墩上的装饰,像这条巷子的看守者,静悄悄的,你都感受不到她的存在。
可她又确确实实的是存在着的。
此后上高中,村子大部分也拆迁了。我再回去的时候,那条巷子显得很突兀,圆石墩还在,旁边的垃圾堆也还在。什么东西变了又好像没变,总之也没有觉察出一点儿痕迹。吃饭的时候,无意想起问我奶奶:“那个大大在哪呢?”“前几个月死了,村里吃了一天大锅菜然后就埋了”。我奥了一声,就接着吃饭了。
之前村子也有人去世的,会放一整天哀乐,大早起就开始响,那个音乐一响,我奶奶就会说村里谁谁家的谁谁死了。那天中午就不会做饭了,都去那家吃大锅菜。中午还有人吹喇叭打锣的,我只是觉得很热闹,看着他们家正屋布置成的灵堂,纸做的小人、屋子、汽车,还有一串串金色的、银色的元宝。我觉得这些东西挺精致,很有意思。下午埋人的时候,一长溜披麻戴孝的人跟着,哭的很大声。村里其他人给长队绕出道儿来,看着他们哭。我也曾看过好几次,只是觉得他们哭的太伤心了。也看到过有人在装哭,声音很大,但是一点儿泪珠也没有。第二天这家人又恢复如常,该干什么干什么。
应该就是那样吧,我想着,老人去世的画面大致也是如此吧。子女大声痛哭,可能第二天又过起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每天少了叫老人回家吃饭的功夫。
过了好些年之后,我在失眠的夜里不时会想起这个老人,然后眼泪居然止不住的流啊。这个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老人,想起来却有无以名状的酸楚。这个活过好几十年的老人就那样平静的消失了,想想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就像人生命中短暂的过客,无法让人有太大的起伏,但这人不见了,心里缺会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可能她的家人很爱她、很照顾她,可她的年岁实在太大了,她的子女也有了自己的子女、孙子,便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她身上啦。
那个圆形的老石墩,人们可能有时会在上歇歇脚,说说闲篇。要是没有石墩呢,就站着说、蹲着说、换一个石头坐着说。现在村子都拆迁了,石墩自然也就没啦。谁还会想着,那个石墩它到底会在哪里呢?